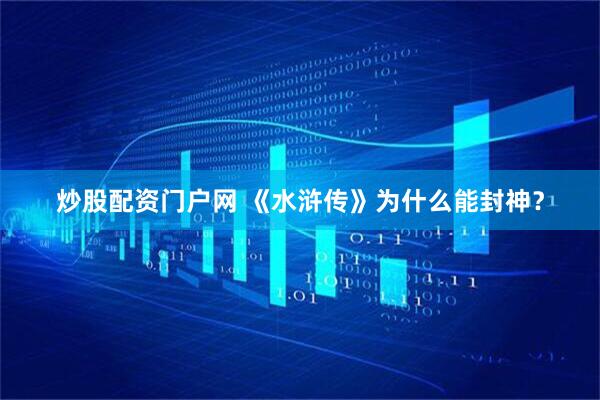“1971年3月15日晚上十点,这份常委名单确定了吗?”周恩来的声音不高,却让屋里所有人都停下了笔。点头,把名单递过去。总理扫了一眼,眉头轻轻一挑:“怎么没有徐信?”短短一句炒股配资门户网,把气氛拉得更紧。尤太忠忙解释徐信正在内蒙古前指执行任务,来不及赶回。周恩来沉吟片刻,只给出七个字:“把他增进去吧。”
这段对话后来在军内流传甚广。许多人都好奇,周总理为何对一个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将领如此看重。要理解这份关注,就得把目光拉回到徐信那条颠簸而又倔强的从军路。

徐信出生于1921年3月的冀北山村。家里二十多口人,全靠父亲挑着米面去集市换钱。9岁那年,他背着布书包进了西街小学,课桌吱呀作响,却挡不住他翻书的热劲。四年后,慈峪镇高小国文教员马秀忠暗中给学生讲《少年中国说》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来历,徐信第一次听到“共产主义”四个字,心里像埋下了火种。
“抗日的队伍在哪儿?”1937年卢沟桥枪声响起,他和十几个同伴没要一分钱路费,循着口口相传的消息一路北上。阜平县城外,他们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民训班学员。16岁的徐信端着还带油漆味的新步枪,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此后八年,他换过七个岗位,从警卫连指导员一直干到团长,勋表上钉满了“模范干部”“特等功”的奖章。
抗战胜利后,内战骤起。大同集宁战役里,徐信指挥22团截击怀仁守军,夜袭三里庄。那天他带着四十来名侦察兵贴着高粱秆匍匐前进,一轮齐射后冲锋号响起,敌军还以为碰上主力,弃城狂逃。战后,杨成武拍着他肩膀说:“年轻人,打出了解放军的锐气。”一种信任,就此埋下。

1949年部队西进,他随63军翻越腾格里沙漠。黄沙没过脚踝,义务兵在行军日志里写道:“团长拿着罗盘蹲在沙丘顶对我们喊,跟我走,天亮必见水。”十几年后,那名义务兵成了63军副参谋长,他常说:自己最佩服徐师长那股不服输的劲。
1951年,朝鲜前线。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,总部表彰187师为“钢铁师”,徐信立二等功。可在凯旋列车上,他对副师长感叹:“死里逃生的人多学一点东西,才对得起兄弟们。”半年后,他被送到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深造。三年留学,除了俄语,他把苏军关于合同战术、军队管理的教材翻得起了毛边。一次讨论课,外军学员问他志愿军为何夜战多、白天少,他笑着回答:“白天打不过飞机,就改在晚上找你们。”教室里哄然大笑,那名外军学员竖起大拇指。
1960年回国,他先在高等军事学院任职,随后被调任63军副军长。正值中苏边境摩擦不断,北京军区为应对热带山岳战争,派他赴越南北方考察。热浪翻滚,他硬是爬完每一座山头,回来写了万余字报告,提出“侧迂穿插、小群多路、靠山借林”的战术构想。报告在军区转发时注明:“徐信同志供稿”。

1966年邢台大地震,凌晨5点,徐信跳上吉普车赶赴震中。为了不伤到被埋群众,他要求官兵徒手刨瓦砾。手指磨烂了,他便把纱布一缠继续干。余震来袭,县委办公楼裂出新缝,他却陪同周恩来在裂缝中间的简易指挥部听取简报。屋顶吱呀作响,大家劝总理出去,总理摆手:“时间宝贵,让徐信说完。”几天后,灾区搭起第一批防震棚,人们把写着“子弟兵恩情”的锦旗送到部队大门口。徐信没收下,他说:“救人天经地义。”
到了1970年底,北京军区换防,徐信走马上任参谋长。仅三个月,内蒙古党委筹备进入关键期。尤太忠携材料进京,周恩来翻阅至常委名单时发现徐信缺席,于是有了开头那句追问。外界常把这看作周总理对基层战功将领的格外体恤,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:那几年内蒙古局势复杂,需要一位既熟悉边疆又懂军事的“老成分寸”来稳定人心。徐信正好合适。
1973年,他回到北京军区,专抓作战、情报、外事。一次会议讨论华北防务,他指着地图对杨得志说:“晋北这条折线,不扎紧就是漏勺。”一句玩笑话,却让部署得以微调。1978年,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,从穿草鞋的少年,到肩扛三星的将军,这条路走了整整四十一年。

1988年授衔那天,邓小平亲自签署命令,徐信被授予上将。合影时,他悄悄把军帽往后压了压,对身边年轻将校笑道:“别看我头发白,脑子还灵。”2005年11月18日,85岁的徐信在北京病逝。追悼会上,有人提起周总理当年那句“把他增进去”。这句话像一把钥匙,开启了徐信在内蒙古、在北京军区、在总参的后半生,也折射出共和国对实干者的珍惜。
纵观徐信的履历,有血火,也有书卷;有沙场,也有课堂。两条线并行,交汇于一个“敢”字:敢打、敢学、敢担。或许正是这种锋芒与沉稳并存的品质,让周恩来在深夜的灯光下提出那句看似简单却分量十足的追问。
配资指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